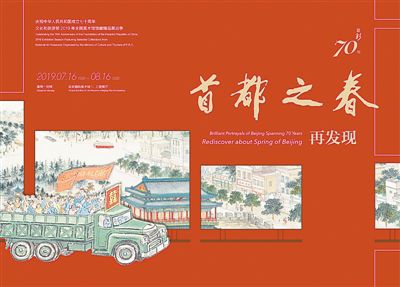
“京彩70年——《首都之春》再發現”展覽海報 北京畫院美術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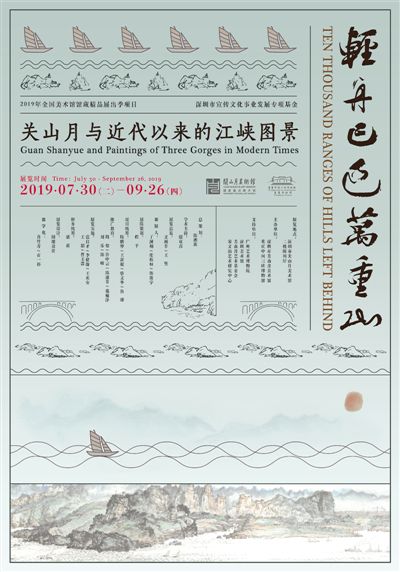
“輕舟已過萬重山——關山月與近代以來的江峽圖景”海報 關山月美術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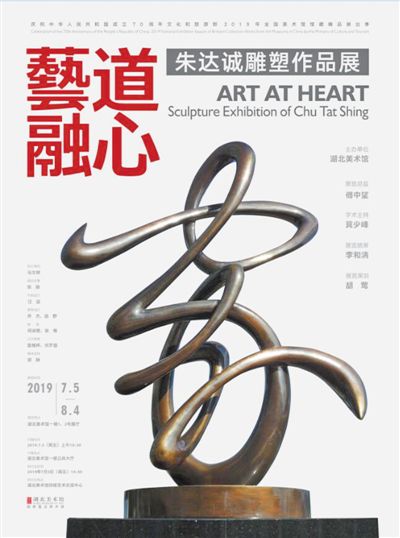
“藝道融心——朱達誠雕塑作品展”海報 湖北美術館
【編者按】
文旅部主辦的2019年全國美術館館藏精品展出季活動項目在京驗收。今年各館推出的展覽項目的共同特點是,都加強了整體策劃。隨著美術館公共服務功能的深化,美術展覽越來越豐富,人們對高質量展覽的期待越來越高,業界對展覽評價體系也逐漸走向深入,好的展覽,策劃成為必不可少的環節。
展覽為什么要“策”?好的展覽,如果沒有經過策劃和設計,就無法有效傳達給觀眾,展覽想說的話就變成不可聽、不可看、不可讀。大的美術館資源豐富,策展彈性和靈活度相對較高,但是對于一些名家館、地方館來說,藏品相對有限和單一,如何辦出內容豐富、觀眾愛看的展覽,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本期我們邀請北京畫院副院長吳洪亮,關山月美術館館長陳湘波與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學研究部主任于洋來談一談策展的挑戰、經驗及思考。
本期主持:
張玉梅、于園媛
本期嘉賓:
吳洪亮 北京畫院副院長
陳湘波 關山月美術館館長
于洋 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學研究部主任
問:在藏品相對有限的情況下,每年都要做展覽,怎么才能做出新意,如何挖掘展覽的內容價值,做深做精,使展覽不是“炒冷飯”,而是年年“有得看”?
吳洪亮:“以個案構建全景”的研究方法,我稱其為“一葉知秋”。我們的策展理念是以20世紀中國藝術發展歷程為“經”,以美術大家為“緯”,從“縱橫”兩個方向出發,以研究性個案展覽的形式由點及線串聯成為一條相對清晰而完整的脈絡。
從廣度看,我們跳出了北京畫院藏品的范疇,積極與全國多家美術館合作。比如,今年舉辦的“越無人識越安閑——齊白石筆下的人物神情之二”展,我們聯合了故宮博物院、中國美術館等十一家國內重量級文博單位及藝術機構,還原了最全面的、不同時期的齊白石人物畫面貌;從內容上看,我們以研究帶動展覽資源的再整合,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力圖挖掘出更多不同層面的齊白石藝術。如去年北京畫院與徐悲鴻紀念館共同推出的“白石墨妙·傾膽徐君——徐悲鴻眼中的齊白石”專題展,這個展以徐悲鴻舊藏齊白石作品為基礎,同時配合展出北京畫院收藏的齊白石、徐悲鴻作品,將兩家藝術機構收藏的齊白石藝術精品70余件(套)匯聚一堂,并通過相關作品、文獻、信札,全面梳理兩位藝術大師相識、相交、相知的詳細過程,這為觀眾了解徐、齊二人的藝術特色與交往提供了一次非常難得的機會。
陳湘波:我們將關山月作品研究,放在20世紀中后期中國美術發展這一宏觀的歷史框架之中,以年度學術專題展的形式,深化和拓展對“關山月與20世紀中后期中國美術研究”課題的學術把握,這不僅使關山月研究這一課題獲得了歷史的厚度和時代的縱深,也為20世紀中國美術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亦是深圳建市40周年,關山月美術館以館藏關山月《江峽圖卷》及其晚年表現長江三峽的畫作為基礎,攜手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推出“輕舟已過萬重山——關山月與近代以來的江峽圖景”。展覽同時還展出各兄弟美術館借展的包括傅抱石、黎雄才、亞明、錢松喦、宋文治、陸儼少等同代藝術家的相關題材的作品,旨在探討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面對長江三峽題材,不同的藝術家通過各自的思考和實踐,來處理傳統技法與現實關系的艱辛探索,探討中國畫筆墨的傳承與發展。
于洋:我認為一個好的展覽至少應該具備三個特質:
首先,一個好的展覽取決于展覽主題的問題意識和學術價值,及作品本身的質量和高度,這是由策展人對于藝術作品的審美判斷力即“眼力”所決定的。尤其對于那些群展或大型主題展覽來說,藝術家及其作品的篩選與甄別是極為重要的工作,也是策展工作中最見功力的一環。其次,要看展覽是否引起了觀者的思考、關注與討論,或帶來有益的啟蒙,開啟新的認知空間和角度。這一點依賴于策展人通過展覽明確表述其文化針對性與學術主題的能力,以及對于展覽主題的理論深化程度與發掘能力。最后,要看展陳布置的現場效果是否吸引觀眾,這里也包含了展覽宣傳手段與各方面投入的精力。一個展覽的展示秩序和營造出的氛圍,應按照某種學術線索層層展開,構成藝術作品的有效集合。與此相對應的,是當下很多展覽對于作品展示排列的粗疏,有些展覽僅僅是將一些藝術家的現成作品湊到一起,作品之間缺乏內在聯系,也往往與展覽題目不符,展覽的效果因此大打折扣。
問:現在各種各樣的美術展覽豐富多彩、五花八門,觀眾的審美品位也趨向多樣化,公立美術館怎么在激烈的競爭中把觀眾吸引來、留得住?
吳洪亮:首先,要在五花八門的展覽中找到美術館自身的定位。像北京畫院這樣的學術創作研究機構,如果只做齊白石會顯得單薄,最終我們確立了以齊白石為中心,逐步延伸到中國20世紀美術史,進而拓展到中國古代美術及世界美術史研究中。
就做展覽來說,我們希望用展覽來講好故事,展覽中宏大的敘述方式是需要的,但最終是要落在實處,用細節把狀態勾勒出來。如北京畫院美術館在2015年做的“大愛悲歌——周思聰、盧沉《礦工圖》組畫研究展”,《礦工圖》是一部在20世紀中國美術史上被視作揭露侵略罪惡、為人民苦難控訴的里程碑式力作。當時的展廳呈現以一種暗沉的氛圍展開,展覽主題墻上有鏤空的“叉”,叉子代表死亡,叉子中兩直線的撞擊和基本色調我們都是按照《礦工圖》的顏色做的,這個思路其實也來自盧沉、周思聰在上世紀80年代初所研究的“水墨構成”,叉子的形狀和畫中的結構有所呼應。而展廳正中間恰到好處地擺放了一支紅玫瑰點亮了整個展覽的暗沉,也讓展覽從“悲歌”落到了“大愛”上。從關注策劃到關注呈現,這個過程不僅要有學術研究的支撐,更是要以觀眾的視角對細節進行考慮與反復推敲,才能真正讓人感同身受,更好理解展覽,從而喜歡這個美術館。
陳湘波:我們注意到近幾年,美術館公共資源的價值正在發生一些悄然變化,已經不僅僅是一個觀看、教育、審美的場所,還兼顧著其他一些社會需求。我們在展陳上下足了功夫,應對挑戰。例如今年的展出季,我們開發了一些具有特色的文創產品,制作了船票、公教小冊子、供觀眾賞玩體驗長卷的區域、供觀眾拍照留影的形象墻等等。這些設計不僅能加深展覽的立意,幫助觀眾理解展覽,也具有一定的獨立審美價值,是吸引觀眾的重要媒介。公共文化服務一直是關山月美術館工作的出發點和目的,展覽公教團隊根據青年觀眾、家庭觀眾、學生團體等不同類型觀眾和特點推出了豐富多元的公共教育活動。通過線上導覽為大眾提供一對一導賞服務,提升參觀體驗;為志愿者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培訓和實踐;通過互動游戲、教育戲劇等創新教育手法,幫助家庭觀眾,特別是兒童了解展覽的內容及其深刻含義;研發館校合作課程,將展覽內容與小學地理、語文、音樂等學科進行創造性結合,充分利用展覽教育資源為學校團體服務。
于洋:美術展覽繁榮局面的表象之下,仍然需要內容的深掘和形式的創新。和當下的藝術創作一樣,藝術展覽也需要“去模式化”,特別是一些主題展和群展,如果只是“完成任務”式的“照本宣科”,就無法在多元文化和全媒體時代的當下吸引更廣泛的觀眾群,也就不能更好地實現藝術作品展示的有效傳播。
因此,展覽籌辦方尤其是公立美術館更應該放下姿態,加強創意,多做受眾調研,了解觀眾的興趣點和接受水平,把握和運用好新興文化形態的媒介手段。以當下很多展覽行之有效的方法來看,設置公共講座、專家導覽、親子活動、互動展示區域,乃至設立專供合影留念的“打卡”專區等,都是讓更多觀眾走進美術館的方法。
事實上,當下一個好的展覽,即便是主要面向專業領域的美術展覽,也不能滿足或停留于“陽春白雪”“曲高和寡”,而是要想辦法將精英性與大眾性相結合。一個好的展覽和一件好的藝術作品一樣,深入淺出、雅俗共賞才是藝術傳播的理想狀態。
問:美術展陳列的時間周期是有限的,能夠走進美術館空間看展覽的人也是有限的,那么如何運用高科技等手段延長展覽的生命周期,使它的傳播效果更廣泛、周期更長?
吳洪亮:美術館的“數字化生存”已成為一種既定事實。它給我們帶來了美術館與觀眾的新時代,可以用三個“更”來總結,即“更細節”“更豐富”“更長久”。所謂“更細節”,就是指可以對作品觀看得更深入,包括畫面的每一個肌理,甚至紙的立面效果;“更豐富”是指可以提供與作品有關的大量信息,以及從人類學、社會學等角度對作品的分析以及大量的相關資料;“更長久”是指觀眾可以24小時關注美術館的展覽以及作品,甚至展覽在結束之后,還可以作為一份資源得以無限利用及延展。
除了宏觀層面展覽的整體虛擬化以外,數字技術也在具體的展陳方式上彌補了傳統實體展覽缺乏互動性、過于刻板的問題。北京畫院在今年舉辦的“越無人識越安閑——齊白石筆下的人物神情之二”展開幕當天,上架了一批齊白石人物畫表情包以供觀眾免費下載使用。這批表情包的原型皆來自北京畫院院藏的齊白石人物畫,所有形象都能夠在展覽中見到。這種互動模式,不僅能夠讓觀眾在欣賞畫作之余產生深刻共鳴,從而更好地理解齊白石的畫中趣味與情境,并且它的效果是持續性的,通過觀眾之間的日常傳播與互動分享,齊白石的藝術就這樣走進了大眾的社交生活中,這就是一種很好的宣傳及傳播途徑。
陳湘波:我們館很早就開始探索數字美術館的建設。展覽的信息、圖片、文獻我們會放到微信上,觀眾通過微信就可以獲得導覽,另外我們也會制作VR展廳、在線展廳,這樣展覽就不會局限于時間和空間,生命周期得到極大延長。
本次展出季及公共教育受到各界媒體、機構、團體的廣泛關注和好評,報紙、互聯網、社交平臺、視頻渠道、App、微信、微博等媒體及渠道發行和曝光量達到280萬次。我們認為展覽的生命周期還關乎展覽的深度和學術性,一個不深入的、表面的展覽是不會有很長的生命周期的。學術研究這塊也是我們非常重視的焦點,每次展出季活動我們都會邀請全國的一線學者做深入的研究,我們的研討會不是茶話會、座談會,每位學者都提交論文做深入發言。最后我們會將作品和文章編輯成畫冊,這樣兼具藝術性和學術性的出版物才是保存展覽生命的最好載體。
于洋: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美術展覽都面臨著媒體時代的傳播考驗,甚至相當一部分展覽都遭遇過開幕熱鬧平日無人、“開幕即閉幕”的現實窘境。親臨現場觀展的受眾是有限的,更多人需要通過媒體、網絡空間的虛擬展場平臺了解與觀賞展覽。但另一方面我認為,高科技的新媒介呈現手段,在當下更多的實際價值是宣傳推廣、輔助和延展現場展覽的功能。好的展覽應該如同一本書,可以被隨時翻閱,而展覽畫冊和虛擬展示平臺,可以起到這樣的作用。但美術館實地觀展體驗,尤其是面對藝術品原作的實體感知,往往是新媒介虛擬展示所替代不了的。因此,高科技的虛擬展示等手段不能喧賓奪主,還是應該在實體展覽內容上下大功夫。
在當下的文化語境與時代風尚影響之下,一個好的藝術展覽既需要對于國際化的規范與規則的學習、借鑒,同時也需要充分“接地氣”,呈現本土的、真實的社會文化問題。無論傳統還是當代、個展還是群展,好的作品、恰切的呈現,加之深入的思考發掘才是展覽的重中之重。
注: 本站發表文章未標明來源“成功書畫家網”文章均來自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我們刪除,聯系郵箱:1047780947@qq.com
隴ICP備17005074號隴網文(2016)6819-012號
2018 www.notedseed.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