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懷山水畫墨色清疏淡遠,格調高雅,畫面猶如霧嵐籠罩般的清淡氣息給人以古雅、詩意的視覺享受。他鐘情于山村,并用畫筆表現著山村的靜謐與和諧,展現出山村人的淳樸與善良。他用精神的自由與超然的心境為觀者營造出了渺遠而空靈的藝術境界,覓得了一片純美的心靈凈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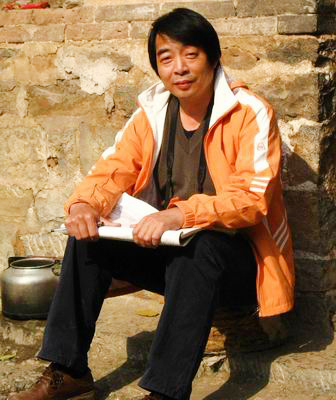
董振懷近照
記者:董老師,您的山水作品多描繪古老山村的景象,筆墨孕育出質樸而厚重的山村魂。您把山村題材貫穿到藝術創作的整個過程,想要表達怎樣的感情寄托?
董振懷:畫乃心物,物有情生。畫乃畫者情感之表現,文化之積淀,靈性之迸發。
我出生在平原,卻與太行山區有著無法割舍的感情,我第一次踏進山區時,沒有被崇山峻嶺所震撼,也沒有被奇峰怪石所折服,卻被這古老的山村所打動。這兒有成片錯落有致的石頭房,青赭色的石頭,青黑色的瓦片,一塊塊石頭記錄著山村人的辛勞,一片片的青瓦展示著山村人的智慧,顯現出古老山村的厚重與魂魄。為此我畫了一系列的關于山村題材的作品,如《喜慶山村》《祥云山村》《希望山村》《春風吹進山窩窩》等。我鐘情于山村,用手中的畫筆去描繪山村人們的喜怒哀樂,山村的晨霧晚霞,山村的裊裊炊煙,山村的牛羊雞鴨,從某些方面也表達了我對家鄉的眷戀。
我畫山村很少對景寫生,更多的是用心去體悟,用腳去丈量,默默的走在山村的石階上、小巷里,靜靜地坐在農家小院里,感受著山村的寂靜,穩穩地捧著鄉親們盛滿米粥的大海碗,品嘗著新鮮的天然美味,吸允著這里甘甜的山泉。我輕輕的踏著先民們走過的臺階,遙想著先民們過去艱難的歲月,獨自翻山越嶺去尋找山村的古老,融入他們喜慶豐收的隊伍,分享他們的快樂,我甚至推起碾子,親身體驗著他們日常生活的辛勞,享受著這里的寧靜,用筆描繪著古老山村的歷史,用墨表現著山村現代的變化,用心體悟著鄉親們的淳樸與善良。
記者:中國山水畫重在意蘊,意在筆先,畫盡意在,旨在詠情。您如何理解中國山水畫中的意境表達?
董振懷:中國山水畫是中國人情思中最為厚重的沉淀。游山玩水的大陸文化意識,以山為德、水為性的內在修為意識,咫尺天涯的視錯覺意識,一直成為山水畫演繹的中軸主線。從山水畫中,我們可以集中體味中國畫的意境、格調、氣韻和色調,再沒有哪一個畫科能像山水畫那樣給我們以更多的情感體驗。山水畫便是民族的底蘊、古典的底氣、我的圖像、人的性情,其起源于中國傳統美學思想重要范疇。在傳統繪畫中作品通過時空境象的描繪,在情與景高度融匯后所體現出來的藝術境界。
“意”是藝術作品的靈魂,具有高低、深淺,文野之分。立“意”是畫家們認識生活的結果,是畫家在感情認識的基礎上提煉、概括、升華而形成的對美的認識和理解。在生活實踐中所產生感情是繪畫作品所必需的。“境”作為美學范疇提出的,標志著意境說的誕生。“意境”被稱之為山水畫的靈魂,畫論中首用“意境”概念的是清人笪重光,他在談實境、空境、真境、神境時特別強調了“空”和“虛”:“空本難圖,實景清而空景現;神無可繪,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畫處多屬贅疣;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
意境不僅只是顯露在有我之境,而且也表現于無我之境,也表現于氣韻。“氣韻生動”是相當廣義的,就是講作品有神韻,有情趣,或天真爛漫、活潑奔放,或明潤郁蔥、幽曲蒼勁。明朝顧凝遠講:“有氣韻則有生動,氣韻或在境中,抑或在境處。”就是指意境和整個畫面的布局神韻是難分難解的。石濤講述得則更深刻:“作書作畫,無論先輩后學,皆以氣勢得之,精神燦爛”。李可染先生也在《山水畫的意境》一文中明確地為意境下了定義:“意境是什么?意境是藝術的靈魂,是客觀事物精髓的集中加上人的思想感情的陶鑄,借景抒情。經過藝術加工,達到情景交融的美的境界,詩的境界,這就叫做意境”。

董振懷作品 價格協商
記者:董老師,您的山水畫作品,構圖精妙,用筆細膩密致,以純水墨的糅合、濃淡相宜的渲染出山的遠近層次關系,營造出蒼潤、古樸的視覺效果,在創作中,您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董振懷:談到這個問題,我寫過一篇文章叫《淡抹韻致墨浸天然》探索淡墨山水之美,在這里我節選一部分與大家共同探討水墨強大的表現力。
近些年我多以淡墨入畫,淡墨之美在于格調之高,格調之高在于淡雅,它與濃重之墨是相對而處的,但并非相互傾軋。我所追求的淡墨山水,一是畫面中所表現出的輕煙淡嵐,云蒸霞蔚的自然景象;二是追求胸中渺遠和空靈,體味猶如霧嵐籠罩般的清淡氣息,這也是繼承前人與自身審美追求融合的產物。畫家作為一個藝術家,與禪僧作為一個徹悟者相通,都要求精神上的完全解脫,要求人的生命本質與禪的形式完美契合,要達到如此奇妙的境界,才能領略到繪畫作為藝術的真諦,這是我為之一求的境地,我希望用水墨為人們提供一個南北皆融的詩意的棲息地。
在山水畫立意中,我強調自然的自在的精神,強調自然給人們在想象和夢幻方面提供的啟發。我努力用傳統的筆墨表現現代人的意識,表現出江南山水的靈秀和北方山水的蒼茫,一切都因此而顯現出靜謐祥和的狀態,這是我內心憧憬的物質性解化,是精神家園圖景的構建。從淡遠、氣韻而至于“平淡天真”,以輕松自然的形式展現我閑適自然的心態。我追求“北宗”繪畫沉穩而凝重的構圖氣勢,講究“南宗”厚而華潤的筆情墨趣,師造化后得心源。
我曾數次深入太行,游歷黃山,到江南園林、杭州西湖游玩,去徽州古鎮,到黃土高原去寫生采風。面向自然,面向生活,切身體會自然的美妙景象。晨霧彌漫,雨洗山村,山體樹林的飄渺漸隱令我陶醉,石濤講“搜盡奇峰打草稿”,搜盡是廣收博取,“打草稿”是認真選擇,提煉取舍。所以我除了表現山村之外,還常常借助于小橋流水、江南園林、西湖美景、水墨徽州等濃郁生活情趣的場景,讓人們體味輕松、超脫、柔和的清新氣息。
我的山水畫不論表現什么內容都統一在淡墨的韻致之下,“虛實相生,無畫處皆成妙境”(清笪重光語),我的畫在構圖上虛中見實,實而不塞,實中見虛,虛而不空。一段煙云,一抹遠山都入畫意。我畫過很多春、夏、秋、冬的作品,以表現春播、夏種、秋收、冬藏之意,我追求四季的清新與透澈。
中國畫崇尚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的情感色彩。摒棄功利之心,洗盡塵俗之念,人才會有雅心、雅風、非閱歷豐富,技藝純青,不能為平淡之美。而在物欲橫流,人心浮躁的時代,我們每一個人都應心懷淡泊,不為名利所困,守住心中那片寧靜,將淡淡的心情帶進生活,便有了恬淡樸實的性情,并在廣闊的空間中自由地進行精神創造,畫面中也才會充盈著古雅,簡淡的氣韻和自然樸素之美。
中國畫應該重新回到重視繪畫品格,藝術氣質,美學修養的堂堂大道,畫家應從傳統文化精神的高度入手,通過對傳統筆墨的領悟和學習,用師造化的視角,再通過持之以恒的追求,最后達到“由技而進乎道”的境界,就是淡抹韻致、墨浸天然這種追求的體現和嘗試。

董振懷作品 價格協商
記者:在我國文化大繁榮大發展的背景下,甘肅致力于建設“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加快甘肅文化大省跨越轉型發展,近期又舉起了打造“敦煌畫派”的旗幟。您對甘肅打造“敦煌畫派”有什么看法和建議?
董振懷:甘肅像一塊瑰麗的寶玉,鑲嵌在中國中部的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內蒙古高原上,東西蜿蜒1600多公里,縱橫45.37萬平方公里。甘肅有群山峻嶺所環抱山嶺、有江河奔流,有一望無垠的遼闊草原、有莽莽漠漠的戈壁瀚海、有郁郁蔥蔥的次生森林、有神奇碧綠的湖泊佳泉、有江南風韻的自然風光,也有西北特有的名花瑞果。
敦煌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記得考大學復試時方惠敏老師就問的關于敦煌問題,這也是我與敦煌的緣分吧。甘肅有著悠久歷史文化積淀,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重要發祥地,莫高窟、羲皇故里麥積山、陽關鎮等都是不可錯過的文化旅游勝地。同時甘肅也是一個少數民族聚居地,少數民族文化豐富多彩、各具特色,敦煌又是世界聞名的佛教文化寶庫,所以打造“敦煌畫派”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從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開始張大千等人借鑒敦煌藝術進行創作,到董希文所繪的《哈薩克牧羊女》吸收了北魏、西魏敦煌壁畫的風格,還有1959年敦煌研究所的常書鴻、段文杰、史葦湘、關友惠、李其瓊、萬庚育、歐陽琳、霍熙亮等老藝術家們創作了《姑娘追》和《獵歸》兩幅作品,其中就是以敦煌壁畫的唐代風格為主,這是敦煌畫派開宗立派應該繼承的藝術特色,希望敦煌畫派的作品能達到深沉厚重,氣勢恢宏,色彩豐富,絢麗輝煌的藝術高度,也希望敦煌畫派早日創作出更多的優秀作品。
董振懷,1962生于河北滄州,1989畢業于河北師院美術系國畫專業。現為中國美協會員,工藝教研室主任,民族畫院特聘畫師。《喜慶山村》參加第二屆全國中國畫;《赤岸寄情》獲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美術作品展優秀獎;《歡樂山村》參加2005年全國中國畫展;《秋染堡壘村》參加抗戰勝利60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希望山村》參加第三屆全國畫院美術作品展;《山村寄情》參加2003菜鄉情全國名家提名展;《高山仰止》參加2001年第四屆山水畫展,獲創新獎;《山村擁翠》參加2004年全國名家精品展,獲精品獎。(記者 張琴琴 校對 馮宜玉)
注: 本站發表文章未標明來源“成功書畫家網”文章均來自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我們刪除,聯系郵箱:1047780947@qq.com